子思,名伋,孔子之孙。思想家,著名儒家学者,战国初年鲁国(今山东曲阜)人。子思早年应该在鲁国一带活动,成年后,曾有一段时间在卫国活动。关于子思在卫国的活动,史书多有记载,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:“子思居于卫,有齐寇。”《孔丛子·抗志》:“卫君问子思曰:‘寡人之政何如?’”晚年像其祖父一样,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国——鲁国,受到鲁穆公的礼聘。居卫和为鲁穆公师,成为子思一生中的两个重要阶段。
子思与其祖父一样,有著作传世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曾记录有“《子思》二十三篇”,按照古书体例,这二十三篇的《子思》当为弟子对子思言论、作品的记录和整理。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旧唐书·艺文志》中,也记录有《子思子》七卷,说明其书至少在隋唐时尚存,只是二十三篇的《子思》与七卷本的《子思子》关系如何,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看法。不过至迟到南宋时,二十三篇的《子思》与七卷本的《子思子》可能均已不传,而出现了汪晫根据《礼记》、《孔丛子》等书的辑本。这样,《子思》的原来面貌如何,已不被人们所知,而《子思》包含了哪些作品,也成为学者不断探究的问题。根据史书的记载和新出土的文献,目前可以确定与子思有关的作品有以下几种:
(1)《中庸》。关于《中庸》出自子思,史书多有记载。如司马迁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“尝困于宋,子思作《中庸》”。《孔丛子》也有子思“困于宋”,作“《中庸》之书四十九篇”的说法,与《史记》记载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。郑玄认为《中庸》是“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,以昭明圣祖之德”(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引郑玄《目录》)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引沈约之言:“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,皆取《子思子》。”说明《中庸》曾是《子思子》中的一篇。这种说法在宋代被学者广泛接受,如朱熹认为“《中庸》之书,子思之所作也”(朱熹:《中庸章句·序》)。后清代学者袁枚、叶酉、俞樾等人根据《中庸》中有“载华岳而不重”、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等语,怀疑《中庸》一书晚出,非子思所作(参见蒋伯潜:《诸子通考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,第332—333页)。华岳,按照传统的说法,是指华山与吴岳,战国时均在秦国境内,而根据史书记载,子思主要在邹鲁宋齐一带活动,足迹未尝入秦;至于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,与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始皇二十六年“一法度衡石丈尺,车同轨,书同文字”、琅邪碑石“器械一,同书文字”相似,明显是秦国统一后的用语,由此认为《中庸》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乃至西汉时期。这一观点由于有比较有说服力材料的支持,在当代学者中影响很大。但“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。除了少数书籍立于学官,或有官本,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变化。很多书在写定前,还有一段口传的过程。尤其在民间流传的,变动尤甚。故《中庸》的个别文句也不排除是后来窜入的可能。所以,在有各种数据明确记载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的情况下,仅仅根据一两句言论,便断定《中庸》一书晚出,显然难以成立。
(2)《缁衣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
《隋书·音乐志》载南北朝梁沈约奏答曰:“汉初典章灭绝,诸儒捃拾沟渠墙壁之间,得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,即编次以为《礼》,皆非圣人之言。《月令》取《吕氏春秋》;《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防记》、《缁衣》皆取《子思子》;《乐记》取《公孙尼子》;《檀弓》残杂,又非方幅典诰之书也。”七卷本的《子思子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、旧唐书·艺文志》均有著录,说明其书至少隋唐时尚存,沈约应该还可以看到,其说应是有根据的。唐代《意林》一书,引用《子思子》多处,其中一条见于《缁衣》。《文选》李善注也引《子思子》两条,都见于《缁衣》。故后世学者多信沈约之说,清代黄以周辑《子思子》七卷,以《缁衣》为其内篇卷四。黄氏认为:“《文选注》引《缁衣》两事,《意林》所采《子思子》十余条,一见于《表记》,再见于《缁衣》,则梁沈约谓今《小戴·中庸》、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四篇类列,皆取诸《子思》书中,斯言洵不诬矣。”郭店竹简《缁衣》发现后,一定程度上为此说提供了证据。根据发掘报告,郭店一号楚墓的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三世纪初,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断定其不晚于公元前300年,考虑到书籍有一个流传过程,则其书写时间可能还会更早(李学勤:《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》,《中国哲学》第20辑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),基本在子思(公元前483年至前402年)生活年代之内。因此,《缁衣》出于子思之手完全可能,而《缁衣》一旦被肯定,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等篇的归属自然也就清楚了。
不过史书上还有《缁衣》来自《公孙尼子》的说法,学者认为这属于“同文重见”的现象,《缁衣》应该和《荀子·哀公》篇一样,《哀公》篇“虽然收入了《荀子》,但也不妨见于《大戴礼记·哀公问五义》和《孔子家语·五仪解》。因为它是孔子事迹言行的记载,在儒家内部,不专属哪一弟子或哪一门派,是一种公共资源。荀子可以用,故收入《荀子》;后世礼家也可以用,故收入《大戴礼记》;孔子家族自应保存,故也收入了《孔子家语》。《缁衣》是孔子语录,孔子弟子公孙尼子将其整理出来,故其后学可以将其收入《公孙尼子》一书,所以就有了刘瓛的《缁衣》公孙尼子所作说。子思用其祖父之书,实质是通过公孙尼子一辈孔子弟子的笔记接受孔子之教,视为‘家学’,后学将其纳入《子思子》一书,于是就有了沈约的《缁衣》‘取《子思子》’说”(廖名春:《〈缁衣〉作者问题新论》,《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》,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版,第64页)。
(3)郭店竹简《五行》。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曾发现有《五行》一篇,在“经”之外还有“说”,魏启鹏先生曾根据其思想特点断定为“战国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”(魏启鹏:《〈德行〉校释》,巴蜀出版社1991年版,第105页),庞朴先生则指出文中“仁义礼智圣”即是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中所批判子思“案往旧造说,谓之五行”的“五行”(庞朴:《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》,《文物》1997年第10期),揭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。但由于马王堆汉墓年代较晚,又没有更多材料可分别“经”、“说”的著作年代,故当时学者往往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,倾向认为是孟子后学的作品,年代约在战国后期,甚或在西汉初期。郭店竹简《五行》出土后,对于确立《五行》的作者有两点重大推进,一是与帛书本相比,竹简本有“经”而无“说”,说明《五行》“经”的部分成书年代应当更早,根据考古学者的意见,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3世纪初,竹简制作时代又早于墓葬时代,而简文成篇的时间更在竹简制作之前,这已很接近子思生活的时代了,将其归为《子思》完全可能。二是竹简本明确题有“五行”二字,排除了“德行”或其他命名的可能,表明其所谈论的仁义礼智圣就是古代的一种五行说。《五行》篇可归于《子思》的关键,就在于其所谈论的仁义礼智圣五行,即是荀子在《非十二子》中批判的“子思倡之,孟轲和之”的五行,《五行》篇篇名的确定,对于确定这一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
此外,《五行》与子思有关还有其他一些旁证。例如,《五行》的思想与“子思作《中庸》”之“诚明”部分多有相近。《五行》与《中庸》之“诚明”所表达的思想是一致和相近的,其差别在于二者使用了不同的概念体系。而一位思想家使用两套概念体系也是可能的。另外,二者文风上也有相似之处,二者除皆为议论体外,还皆喜引《诗》,反映了子思一派的特点。还有,《五行》与取于《子思子》的《缁衣》以及记子思之言的《鲁穆公问子思》同时出土,是否也为其原属《子思》添加一旁证?凡此种种,都显示将《五行》归于《子思》是有一定根据,是可以成立的。
(4)郭店竹简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。《鲁穆公问子思》属于《子思》分歧最少,几乎得到学者的一致认可。如杨儒宾先生所说,“‘从道不从君’是儒门通义,《鲁穆公问子思》此文放到儒家其他典籍,其义亦可兼容。然而,本文明说到子思与鲁穆公问答,我们都知道先秦子书流行问答的语录,而且随时代推衍,文字由简而繁。此篇全文风格特别近似《孟子》一书的叙述,与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等书的对话篇章风格亦颇近似。此文就像《孟子》一书以孟子之名发言一样,其文纵非作者自著,至少也是其弟子所作,所以我们如将作者权归到其名之下,应该是说得过去的。”另外,本篇所记子思“恒称其君之恶者,可谓忠臣矣”的政治主张,与传世典籍中记载子思的批判、抗议精神,以及“有傲世主之心”的精神风貌,若合符节。足可证明,该篇确为子思弟子记录的子思言论,其可靠性不容置疑。退一步讲,即使《子思》二十三篇中原不包括这一篇,那么,它也应属于子思的佚文,其价值也绝不在二十三篇之下,将其归入子思一派的作品中,绝没有什么问题。
(5)《淮南子·缪称篇》(部分)。清人黄以周在辑录《子思子》时,注意到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和子思书的密切关系。他将所辑《子思子》佚文见于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者皆一一注明,其中明见于《缪称训》的竟达十条之多,另有两条与《缪称训》暗合,故指出:“《淮南子·缪称训》多取子思书。”(黄以周辑:《子思子》卷二、卷六)杨树达先生在校读《缪称训》时亦说:“此篇多引经证义,皆儒家之说也。今校知与《子思子》佚文同者凡七八节之多(实十二条——引者注),疑皆采自彼书也。惜《子思子》不存,不得尽校耳。”(杨树达:《淮南子证闻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,第92页)郭店竹简有关子思逸籍发现后,一些学者旧案重提,如刘乐贤认为,“我们虽不能说《缪称》全部取自《子思子》,但可以肯定,《缪称》保存的子思学派思想必定相当丰富。”(刘乐贤:《〈性自命出〉与〈淮南子·缪称〉论“情”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2000年第4期)郭沂则进一步肯定,“《缪称训》主体部分采自子思书”,并断定为《子思子》中《累德篇》。他认为,“将群书所引子思书与《缪称训》相比较,不难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,后者的语义更加完整,甚至在《缪称训》中见于子思书佚文的部分同其上下文浑然一体。这说明,《缪称训》见于子思书佚文之段落之上下文很可能也本属子思书。”另外,《缪称训》频繁地引用《诗经》、《周易》,在《淮南子》中再无第二篇,而“引经证义”,正是子思著作的鲜明特点(郭沂:《〈淮南子·缪称训〉所见子思〈累德篇〉考》,《孔子研究》2003年第6期)。
按,《淮南子》为杂家著作,“其旨近《老子》”,“其大较归之于道”,但又“讲论道德,总统仁义”,即除了道家外,儒家思想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由于参与此书编写的有“诸儒大山、小山之徒”,其将儒家文献编入其中便是很自然的事情。《缪称训》多与《子思子》佚文相合也反映了这一点。不过由于《淮南子》是编纂而成,所以也不排除《缪称训》中夹杂着编纂者个人的发挥,或加入其他来源的材料,但其主体部分或相当一部分来自《子思子》当无疑问。
(6)其他。包括散见于《礼记·檀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说苑》、《中论》中有关子思的内容以及《孔丛子》的一部分。其中《孔丛子》《记问》第五、《杂训》第六、《居卫》第七、《巡狩》第八、《公仪》第九、《抗志》第十主要记载子思的言行,也是比较重要的有关子思的文献,但《孔丛子》的来源较复杂,其内容需要做具体分析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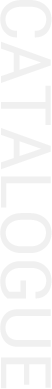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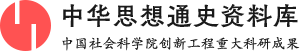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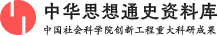
 邮编:100720
邮编:100720 产品咨询:010-84083678
产品咨询:010-84083678 售后客服:2501160687@qq.com
售后客服:2501160687@qq.com
